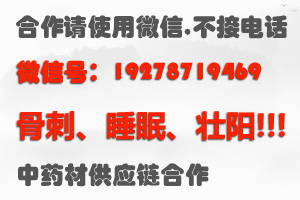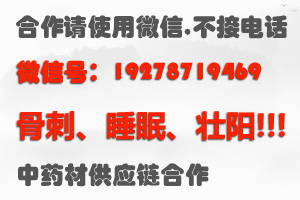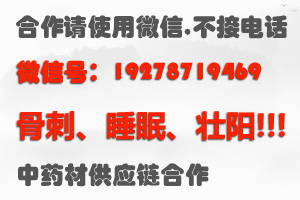三七粉不說二八,為什么說四六不懂而不說三七不懂二八不懂
為什么說四六不懂而不說三七不懂二八不懂古代崇奉“天地君親師”。作為一個讀書人,是一定要銘記這幾項的。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不明就理!而這幾項里面其中以“天、

1,為什么說四六不懂而不說三七不懂二八不懂
2,為什么只有年方二八沒有三七或者二九或者別的什么
3,吃三七粉的禁忌有哪些
吃三七粉的禁忌:孕期婦女禁止使用、感冒期間。女性在懷孕期間,禁止服用三七粉。這和孕婦不能服用很多西藥一樣的道理。風(fēng)寒感冒期間不能服用三七花,因為三七花性微涼,會加重風(fēng)寒感冒,三七粉性溫,風(fēng)寒感冒期間可以服用。而患風(fēng)熱感冒則不宜服三七粉。
三七粉是植物三七(學(xué)名:Panax pseudo-ginseng)的根莖制品,是用三七主根打成的粉。別名田七粉,金不換。性溫,味甘微苦,入肝、胃、大腸經(jīng)。又稱北人參,南三七。人參補(bǔ)氣第一,三七補(bǔ)血第一。一直以來,三七都是一味中藥材。三七的功用,原來可用“止血、散瘀、定痛”六個字來概括。
三七粉是用三七主根打成的粉。生三七適用于跌打瘀血、外傷出血、產(chǎn)后血暈、吐血、衄血等血癥,熟三七適用于身體虛弱、食欲不振、神經(jīng)衰弱、過度疲勞、失血、貧血等。三七粉含多種皂甙,尚含止血活性成分田七氨酸及少量黃酮。
使用三七粉時需要注意:孕期婦女禁止使用:女性在懷孕期間,禁止服用三七粉。這和孕婦不能服用很多西藥一樣的道理。感冒期間:風(fēng)寒感冒期間不能服用三七花,因為三七花性微涼,會加重風(fēng)寒感冒,三七粉性溫,風(fēng)寒感冒期間可以服用。而患風(fēng)熱感冒則不宜服三七粉。
花與粉對比
三七花為生長二年以上的三七尚未開放的花蕾,民間作茶飲用,有清涼、平肝、降壓之效。現(xiàn)代研究表明:三七花是三七全株中含三七皂苷最高的部位,含量高達(dá)13%以上,以Rb族皂苷為主,具有鎮(zhèn)靜安神、抗炎鎮(zhèn)痛、降血壓等藥理作用,常用于治療高血壓、偏頭痛、失眠等癥。它具備三七的大部份功效,但是與三七不能等同,兩者是有區(qū)別的。
三七花 :性涼,味甘、微苦。主要用于清熱、解毒、涼血、免疫調(diào)節(jié)、活血通脈、養(yǎng)生抗衰、消炎鎮(zhèn)痛作用的有效成份。具有顯著的平肝、祛痰、平喘、鎮(zhèn)痛安眠、擴(kuò)冠、抗過敏、排毒養(yǎng)顏等功效。
三七粉:性溫,味苦回甜。補(bǔ)血,去瘀損,止血衄,能通能補(bǔ),功效最良,是方藥中之最珍貴者。三七生吃,去瘀生新,并有止血不留瘀血,行血不傷新的優(yōu)點,熟三七粉可以補(bǔ)身體。
4,為什么說不管三七二十一而不說不管四七二十八呢
5,史上最全的三七粉的功效與作用禁忌詳解
大家都知道三七粉是非常好的藥材,下面我來給大家講講它的優(yōu)點和禁忌。
1.三七對血液和造血系統(tǒng)的作用
三七粉被廣泛應(yīng)用于心腦血管系統(tǒng)疾病的預(yù)防和治療,以其活血、止血和補(bǔ)血功能有關(guān),三七粉中的三七素、和槲皮苷等物質(zhì)是止血成分,而其皂苷類和黃酮類成分則是活血化瘀的物質(zhì)。
(1)三七粉的活血作用
三七粉的功效與作用:三七總皂苷能抑制血小板聚集,其主要有效成分是人參皂苷Rg1及人參三醇型皂苷,通過提高血小板cAMP含量而抑制血小板聚集功能。
(2)三七粉的止血作用
三七粉止血是通過多方面使用實現(xiàn)的。三七根的溫浸液能縮短家兔血液凝固時間,并使血小板數(shù)量增加而有止血作用。
三七能促進(jìn)凝血過程,縮短凝血時間,促進(jìn)凝血酶的生成,使局部血管收縮,促進(jìn)血小板數(shù)目。三七配伍烏賊骨和白芨散有良好的止血作用。
(3)補(bǔ)血作用
三七粉的功效與作用除了活血止血外,還有補(bǔ)血的作用,三七總皂苷有明顯升高白細(xì)胞的作用,PNS對X線照射所致大鼠外周血細(xì)胞和血小板減少亦有保護(hù)效應(yīng)。三七總皂苷可顯著提高巨噬細(xì)胞吞噬率,提高血液中淋巴細(xì)胞百分比,降低白細(xì)胞指數(shù)。Rb1、Rg1可以提高人紅細(xì)胞膜蛋白α螺旋的比例,即增加膜蛋白的有序性,從而改善紅細(xì)胞功能。
2.三七對血管系統(tǒng)的作用
(1)三七粉對心肌的保護(hù)作用
三七總皂苷具有良好的心肌保護(hù)作用,秦氏等研究了三七總皂苷對勞累型心絞痛患者左室舒張功能的影響,結(jié)果表明,三七總皂苷能改善患者的心肌缺血狀態(tài),且能逆轉(zhuǎn)僅有舒張功能不全的早期心衰患者的心功能及已經(jīng)發(fā)生的病理變化。
(2)三七粉抗心律失常作用
PNS對氯仿誘發(fā)的小鼠心室纖顫、氯化鋇和烏賊頭堿誘發(fā)的心律失常均有明顯對抗作用,三七二醇皂苷也有類似效應(yīng)。PNS能非競爭性地對抗異丙腎上腺素加速心律作用,且此作用不為阿托品所抑制,提示其抗心律失常作用并不是通過競爭性阻斷腎上腺素β-受體或興奮M-膽堿受體,而是與心肌的直接抑制有關(guān)
(3)三七粉對血管的作用
三七粉能夠降血脂,防止動脈粥樣硬化。動脈壁內(nèi)皮損傷可能是動脈硬化的始動因素,而高血脂血癥可導(dǎo)致血管內(nèi)皮損傷、脫落或者血小板粘附和聚集。三七總皂苷能明顯抑制低濃度高脂血清對體外培養(yǎng)血管平滑肌細(xì)胞的作用,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及主動脈內(nèi)膜斑塊的形成有一定防治作用。
(4 )三七粉降血壓作用
PNS及Rg1型皂苷均有明顯的降血壓作用,目前普片認(rèn)為PNS是鈣通道阻滯劑,其擴(kuò)血管的機(jī)理可能是阻斷去甲腎上腺素所致Ca?內(nèi)流。
那么三七粉有什么服用禁忌呢?
1.首先對三七過敏的人群不宜服用三七粉,但對三七過敏的人很少;
2.不可過量,用于日常保健,每天3-5克三七粉,用溫水分2次送服;
3.10歲一下兒童不宜長期服用三七粉,三七粉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,10歲以下兒童自身疫力還沒有發(fā)育完善,長期服用可能會影響自身免疫力的發(fā)育;
4.孕期不宜服用三七粉,這和不能服用很多西藥同理。
5.現(xiàn)代醫(yī)家認(rèn)為,在服用三七當(dāng)日,應(yīng)忌食蠶豆、魚類及酸冷食物。由于三七活血化瘀力強(qiáng),故血虛無淤者忌服,血虛、血熱妄行者禁用。
6.土三七、菊三七等也有活血的功效,但是有毒性,誤食會造成肝中毒。
6,問個三七粉的事
東東是好,可口感不好。三七好苦呀
三七具有清熱平肝,養(yǎng)心安神,潤肺,葆青春抗衰老、消除和減少皮膚皺紋及老年斑等功效。 尤其適用于女性的美容、護(hù)膚,是女性最天然的良好美容護(hù)膚養(yǎng)顏產(chǎn)品,它能抗衰老,保護(hù)皮膚,改善皮膚外觀,使皮膚柔軟并增加彈性……也可把三七用于做菜,或是磨成粉和蜂蜜拌勻然后做面膜,長期服用和使用效果更好。 三七粉對女性的作用主要是調(diào)經(jīng)和美容的功效。 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對三七粉美容效果研究證明: 清脂美白:三七清脂因子滲透肌膚底層.清除多余脂舫.調(diào)理脈氣.促進(jìn)血液循環(huán).讓皮膚自然美白 祛皺養(yǎng)顏:三七養(yǎng)顏因子能夠去除皮膚暇佌.煥發(fā)皮膚神采.調(diào)理脈氣.使皮膚更完美無暇 凈白去斑:三七祛斑因子能夠針對因內(nèi)分泌失調(diào)或曬后導(dǎo)致的曬斑.黑頭.雜質(zhì)沉淀等現(xiàn)象有特效 舒緩暗瘡:三七舒緩活血因子能夠促進(jìn)肌膚血液循環(huán).增強(qiáng)肌膚稀薄呼吸作用的同時舒緩暗瘡再生 三七粉美容做法一: 珍珠三七粉面膜 材料: 珍珠末, 三七粉, 靈芝粉, 陳皮粉。 用法: 每種粉一茶匙, 加半只蛋白開勻。 三七粉美容做法二: 取三七粉5-10g,用水,或蛋清,或牛奶,調(diào)和成糊狀,均勻涂于面部,20分鐘洗掉,即可。 三七粉美容做法三:取適量三七粉,邊緩緩加入蜂蜜邊攪拌,直至成為糊狀,直接敷面20-30分鐘。www.ng37.com 解答更為詳細(xì)。
7,鼻子
鼻子
芥川龍之介
談起禪智內(nèi)供的鼻子,池尾地方無人不曉。它足有五六寸長,從上唇上邊一直垂到顎下。形狀是上下一般粗細(xì),酷似香腸那樣一條細(xì)長的玩藝兒從臉中央茸拉下來。
內(nèi)供已年過半百,打原先當(dāng)沙彌子的時候起,直到升作內(nèi)道場供奉的現(xiàn)在為止,他心坎上始終為這鼻子的事苦惱著。當(dāng)然,表面上他也裝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樣子。不僅是因為他覺得作為一個應(yīng)該專心往生凈土的和尚,不宜惦念鼻子,更重要的還是他不愿意讓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。平素言談之中,他最怕提“鼻子”這個詞兒。
內(nèi)供膩煩鼻子的原因有二:一個是因為鼻子長確實不便當(dāng)。首先,連飯都不能自己吃。不然,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飯上去了。內(nèi)供就吩咐一個徒弟坐在對面,吃飯的時候,讓他用一寸寬兩尺長的木條替自己掀著鼻子。可是像這么吃法,不論是掀鼻子的徒弟,還是被掀的內(nèi)供,都頗不容易。一回,有個中童子來替換這位徒弟,中童子打了個噴嚏,手一顫,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。這件事當(dāng)時連京都都傳遍了。然而這決不是內(nèi)供為鼻子而苦悶的主要原因。說實在的,內(nèi)供是由于鼻子使他傷害了自尊心才苦惱的。
池尾的老百姓替禪智內(nèi)供著想,說幸虧他沒有留在塵世間,因為照他們看來憑他那個鼻子,沒有一個女人肯嫁給他。有人甚至議論道,他正是由于有那么個鼻子才出家的。內(nèi)供卻并不認(rèn)為自己當(dāng)了和尚鼻子所帶來的煩惱就減少了幾分。內(nèi)供的自尊心是那么容易受到傷害,他是不會為娶得上娶不上妻子這樣一個具體事實所左右的。于是,內(nèi)供試圖從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來恢復(fù)自尊心。
他最初想到的辦法是讓這鼻子比實際上顯得短一些。他就找沒人在場的時候,從不同的角度照鏡子,專心致志地揣摩。他時而覺得光改變臉的位置心里還不夠踏實,于是就一會兒手托腮幫子,一會兒用手指扶著下巴額,一個勁兒地照鏡子。可是怎么擺弄鼻子也從不曾顯得短到使他心滿意足。有時候他越是挖空心思,反而越覺得鼻子顯得長了。于是,內(nèi)供就嘆口氣,把鏡子收在匣子里,勉勉強(qiáng)強(qiáng)又對著經(jīng)幾誦他的《觀音經(jīng)》去了。
內(nèi)供還不斷地留心察看別人的鼻子。僧供經(jīng)常在汕尾寺講道。寺院里,禪房櫛比鱗次,僧徒每天在浴室里燒澡水。這里出出進(jìn)進(jìn)的僧侶之輩,絡(luò)繹不絕。內(nèi)供不厭其煩地端詳這些人的臉。因為哪怕一個也好,他總想找個鼻子跟自己一般長的人,聊以自慰。所以他既看不見深藍(lán)色綢衣,也看不見白單衫。至于橙黃色帽子和暗褐色僧袍,正因為平素看慣了,更不會映入他的眼簾。內(nèi)供不看人,單看鼻子:鷹勾鼻子是有的,像他這號兒鼻子,卻連一只也找不到。總找又總也找不到,內(nèi)供逐漸地就懊惱起來。他一邊跟人講話,一邊情不自禁地捏捏那尊拉著的鼻尖,不顧自己的歲數(shù)絆紅了臉,這都怪他那惆悵的情緒。
最后,內(nèi)供竟想在內(nèi)典外典里尋出一個鼻子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,好排遣一下心頭的愁悶。可是什么經(jīng)典上也沒記載著目鍵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。龍樹和馬鳴這兩尊菩薩,他們的鼻子當(dāng)然也跟常人沒什么兩樣。內(nèi)供聽人家講到震旦的事情,提及蜀漢的劉玄德耳朵是長的,他想,那要是鼻子的話,該多么能寬解自己的心啊。
內(nèi)供一方面這么消極地苦心自慰,另一方面又積極地想方設(shè)法要把鼻子弄短,在這里就無須贅述了。他幾乎什么辦法都想盡了。他喝過老鴰爪子湯,往鼻頭上涂過老鼠尿。可是不管怎么著,五六寸長的鼻子不是依然耷拉到嘴上嗎?
一年秋天,內(nèi)供的徒弟進(jìn)京去辦事,從一個熟捻的醫(yī)生那里學(xué)到了把長鼻子縮短的絕技。那位醫(yī)生原是從震旦渡海來的,當(dāng)時在長樂寺作佛堂里的供奉僧。
內(nèi)供跟平日一樣裝出對鼻子滿不在乎,偏不說馬上就試試這個辦法。可同時他又用輕松的口吻念叨著每頓飯都麻煩徒弟,未免于心不安。其實,他心里是巴望徒弟勸說他來嘗試這一辦法。徒弟也未必不明白內(nèi)供這番苦心。這倒也并沒有引起徒弟的反感,毋寧說內(nèi)供用這套心計的隱衷似乎贏得了徒弟的同情。于是,他苦口婆心地勸說起內(nèi)供來。內(nèi)供如愿以償,終于依了這番熱心的勸告。
辦法極其簡單,僅僅是先用熱水燙燙鼻子,然后再讓人用腳在鼻子上面踩。
寺院的浴室照例每天都燒水。徒弟馬上就用提桶從浴室打來了熱得伸不進(jìn)指頭的滾水。要是徑直把鼻子伸進(jìn)提桶,又怕蒸氣會把臉(火通)壞。于是,就在木紙托盤上鉆了個窟窿,蓋在提桶上,從窟窿里把鼻子伸進(jìn)熱水。惟獨這只鼻子浸在滾水里也絲毫不覺得熱。過一會兒,徒弟說:“燙夠了吧。”
內(nèi)供苦笑了一下。因為他想,光聽這句話,誰也想不到指的會是鼻子。鼻子給滾水(火通)得發(fā)癢,像是讓屹蚤咬了似的。
內(nèi)供把鼻子從木紙托盤的窟窿里抽出來之后,徒弟就兩腳用力踩起那只還熱氣騰騰的鼻子來了。內(nèi)供側(cè)身躺在那里,把鼻子伸到地板上,看著徒弟的腳在自己眼前一上一下地動。徒弟臉上不時露出歉意,俯視著內(nèi)供那禿腦袋瓜兒,問道:“疼嗎?醫(yī)生說得使勁踩,可是,疼嗎?”
內(nèi)供想搖搖頭表示不疼。可是鼻子給踩著,頭搖不成。他就翻起眼睛,打量著徒弟那腳都皴了,用慢怒般的聲音說:“不疼。”
說實在的,鼻子正癢癢,與其說疼,毋寧說倒挺舒服的呢。
踩著踩著,鼻子上開始冒出小米粒兒那樣的東西。看那形狀活像一只拔光了毛囫圇個兒烤的小鳥。徒弟一看,就停下腳來,似乎自言自語地說:“說是要用鑷子拔掉這個呢。”
內(nèi)供不滿意般地鼓起腮幫子,一聲不響地聽任徒弟去辦。當(dāng)然,他不是不知道徒弟是出于一番好意的。但自家的鼻子給當(dāng)做一件東西那樣來擺弄,畢竟覺得不愉快。內(nèi)供那神情活像是一個由自己所不信任的醫(yī)生來開刀的病人似的,遲遲疑疑地瞥著徒弟用鑷子從鼻子的毛孔里鉗出脂肪來。脂肪的形狀猶如鳥羽的根,一拔就是四分來長。
錯了一通之后,徒弟才舒了一口氣,說:“再燙一回就成啦。”
內(nèi)供依然雙眉緊蹙,面呈溫色,任憑徒弟做去。
把燙過兩次的鼻子伸出來一看,果然比原先短多了,跟一般的鷹勾鼻子差不離。內(nèi)供邊撫摸著變短了的鼻子,邊靦腆地悄悄照著徒弟替他拿出來的鏡子。
鼻子——那只耷拉到顎下的鼻子,已經(jīng)令人難以置信地萎縮了,如今只窩窩囊囊地殘留在上唇上邊。上面滿是紅斑,興許是踩過的痕跡吧。這樣一來,管保再也沒有人嘲笑他了。——鏡子里面的內(nèi)供的臉,對著鏡子外面的內(nèi)供的臉,滿意地腴了腴眼睛。
可是那一整天內(nèi)供都擔(dān)心鼻子又會長了起來。不論誦經(jīng)還是吃飯的當(dāng)兒,一有空他就伸出手去輕輕地摸摸鼻尖。鼻子規(guī)規(guī)矩矩地呆在嘴唇上邊,并沒有垂下來的跡象。睡了一宿,第二天清早一醒來,內(nèi)供首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。鼻子依然是短的。內(nèi)供恰似積了抄寫《法華經(jīng)》的功行,心情已經(jīng)多年不曾感到這么舒暢了。
然而過了兩三天,內(nèi)供發(fā)現(xiàn)了意想不到的情況。有個武士到池尾寺來辦事兒,他臉上擺出一副比以前更覺得好笑的神色,連話都不正經(jīng)說,只是死死地盯著內(nèi)供的鼻子。豈但如此,過去曾失手讓內(nèi)供的鼻子杵到粥里去的那個中童子,在講經(jīng)堂外面和內(nèi)供擦身而過的時候,起先還低著頭憋著笑;后來大概是終于憋不住了,就噗哧一聲笑了起來。他派活兒給雜役僧徒的時候,他們當(dāng)著面還畢恭畢敬地聽著,但只要他一掉過身去,就偷偷笑起來,這樣已不止一兩回了。
內(nèi)供最初認(rèn)為這是因為自己的相貌變了。然而光這么解釋,似乎還不夠透徹。——當(dāng)然,中童子和雜役僧徒發(fā)笑的原因必然在于此。同樣是笑,跟過去他的鼻子還長的時候相比,笑得可不大一樣。倘若說,沒有見慣的短鼻子比見慣了的長鼻子更可笑,倒也罷了。但是似乎還有別的原因。
內(nèi)供誦經(jīng)的時候,經(jīng)常停下來,歪著禿腦袋喃喃地說:“以前怎么還沒笑得這么露骨呢?”
這當(dāng)兒,和藹可親的內(nèi)供準(zhǔn)定茫然若失地瞅著掛在旁邊的普賢像,憶起四五天前鼻子還長的時候來,心情郁悶,頗有“嘆今朝落魄,憶往昔榮華”之感。可惜內(nèi)供不夠明智,回答不了這個問題。
——人們的心里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。當(dāng)然,沒有人對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。但是當(dāng)那個人設(shè)法擺脫了不幸之后,這方面卻又不知怎地覺得若有所失了。說得夸大一些,甚至想讓那個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。于是,雖說態(tài)度是消極的,卻在不知不覺之間對那個人懷起敵意來了。——內(nèi)供盡管不曉得個中奧妙,然而感到不快,這無非是因為他從池尾的僧俗的態(tài)度中覺察到了旁觀者的利己主義。
內(nèi)供的脾氣日益乖張起來了。不管對什么人,沒說上兩句話就惡狠狠地責(zé)罵。最后,連替他治鼻子的那個徒弟,也背地里說:“內(nèi)供會由于犯了暴戾罪而受懲罰的。”那個淘氣的中童子尤其意他生氣。有一天,內(nèi)供聽見狗在狂吠不止,就漫不經(jīng)心地踱出屋門一望,中童子正掄起一根兩尺來長的木條,在追趕一只瘦骨嶙嶙的長毛獅子狗。光是追著玩倒也罷了,他還邊追邊嚷著:“別打著鼻子,喂,可別打著鼻子!”內(nèi)供從中童子手里一把奪過那根木條,痛打他的臉。原來那就是早先用來托鼻子的木條。
鼻子短了反倒叫內(nèi)供后悔不迭。
一天晚上,大概是日暮之后驟然起了風(fēng),塔上風(fēng)鈴的嘈音傳到枕邊來。再加上天氣一下子也冷下來了,年邁的內(nèi)供睡也睡不著。他在被窩里翻騰,忽然覺得鼻子異乎尋常地癢,用手一摸,有些浮腫,那兒甚至似乎還發(fā)熱呢。
內(nèi)供以在佛前供花那種虔誠的姿勢按著鼻子,嘟囔道:“也許是因為硬把它弄短,出了什么毛病吧。”
第二天,內(nèi)供像往常一樣一大早就醒了。睜眼一看,寺院里的銀杏和七葉樹一夜之間掉光了葉子,庭園明亮得猶如鋪滿了黃金。恐怕是由于塔頂上降了霜的緣故吧,九輪在晨曦中閃閃發(fā)光。護(hù)屏已經(jīng)打開了,禪智內(nèi)供站在廊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就在這當(dāng)兒,內(nèi)供又恢復(fù)了某種幾乎忘卻了的感覺。
他趕緊伸手去摸鼻子。摸到的不是昨天晚上的短鼻子了,而是以前那只長鼻子,從上唇一直垂到顎下,足有五六寸長。內(nèi)供知道自己的鼻子一夜之間又跟過去一樣長了。同時他感到,正如鼻子縮短了的時候那樣,不知怎地心情又爽朗起來。
內(nèi)供在黎明的秋風(fēng)中晃蕩著長鼻子,心里前南自語道:“這樣一來,準(zhǔn)沒有人再笑我了。”
經(jīng)典短篇閱讀小組
長按二維碼識別關(guān)注
8,一塊地
一塊地.
芥川龍之介
阿住的兒子是在采茶剛剛開始的時候死去的。兒子仁太郎就像個癱子似的在床上足足躺了八年。這樣的一個兒子死了,人們說是阿住的“來世修好”,阿住本人的確也并不怎么悲傷,當(dāng)阿住在仁太郎的棺材前邊供上一炷香的時候,心里倒有一種如釋重負(fù)般的輕松感覺。
仁太郎的葬禮辦完之后,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兒媳阿民的事。阿民有一個男孩。并且她替臥病的仁太郎把地里的莊稼活差不多全承擔(dān)起來了。如果兒媳現(xiàn)在走了,不用說孩子沒人照顧,甚至連家里的生活也維持不了。因此阿住想,等過了七七四十九天,就給阿民找個丈夫,讓她像兒子在世時一樣,擔(dān)起家里的活來。她想找仁太郎的叔表兄弟與吉作贅婿。
偏偏剛好在頭七的第二天早晨,阿民收拾起出嫁時的東西來了,阿住不禁大吃一驚。阿住那時候正領(lǐng)著孫子廣次在里屋的走廊上玩。給孩子玩的玩具,是從學(xué)校偷來的一枝盛開的櫻花。
“喂,阿民,俺不該把話一直門在肚子里,是俺的錯,可是你,就這么著把孩子和俺扔下走嗎?”
阿住的聲音,與其說是責(zé)備,倒不如說是在訴苦。阿民沒有回過頭來,只是笑著說:“婆婆,看你說了些啥呀!”盡管是這么一句話,阿住是多么放心就別提了。
“是呀,俺想你也不至于這樣……”
阿住還在絮絮叨叨地傾吐著夾雜著怨氣的心愿。同時她的話又漸漸勾起她自己的悲傷來了,幾行淚水終于順著滿是皺紋的面頰流了下來。
“是啊,只要是你愿意,俺也希望一輩子能住在這個家里啊!——還有這么個孩子呢,誰愿意走呢!”
不知不覺地阿民也流下了眼淚,把廣次抱到自己的膝蓋上,廣次好像特別害羞的樣子,一個勁兒惦記著扔在里屋鋪席上的櫻花枝子……
阿民和仁太郎在世的時候一樣,照樣悶頭在地里干活。但是招婿的問題,卻不像阿住打算的那樣容易解決。阿民對這種事兒好像完全沒有興趣。阿住一有機(jī)會,不是悄悄試探阿民的口氣,就是開門見山地和她談意見。然而阿民每次都說:“是呀,等來年再說吧!”馬馬虎虎應(yīng)付過去。阿住對這個自然是既憂愁又高興。阿住一邊顧慮世上說三道四,一邊只好聽兒媳的話,等來年再說了。
但是,到了第二年,阿民除了忙地里的莊稼活,好像什么也不想。阿住以比去年更懇切似的口氣,提出招婿的問題。這其中的原因,是她受到了親戚的責(zé)備和世人暗地里的閑言冷語,使她有難言的苦衷。
“可是呀,阿民,你現(xiàn)在還這么年輕,沒有個男人可過不下去啊。”
“過不下去又有啥法呀!不信你給咱家找進(jìn)一個外人來看看。小廣會很可憐,你也會操心,而俺的操心勞累,就更不用提了!”
“所以呀,俺才想把與吉招來啊,他最近說決不賭錢了!”
“他是婆婆的親戚呀!可是對俺來說終究是個外人吶!哎,俺只好忍耐下去啦……”
“可是話又說回來啦,你這個忍耐,可不是一年兩年的事啊!”
“沒什么啊!這是為了小廣哩。俺現(xiàn)在受點苦,咱家的地就不用分成兩份,就全是小廣的了!”
“可是,阿民呀(阿住每當(dāng)?shù)竭@個時候,都是一本正經(jīng)的,溫言細(xì)語的),別人的閑話可討厭啦。你今天在俺面前講的話,可以仔細(xì)講給別人聽聽……”
她們兩個人的這種對話,不知道談過多少次了。然而阿民的決心,卻反而越來越堅決,沒有絲毫軟下來的樣子。阿民也真的沒有借助男勞力幫忙,自己既種白薯,又割麥子,莊稼活比以前干得更起勁了。還不只如此,夏天喂母牛,即使是下雨天,她也出去割草。這種頑強(qiáng)的勁頭,本身就是眼下對招進(jìn)外人一事所表示的一種強(qiáng)烈抗議。阿住也終于打消了招婿的念頭。當(dāng)然,打消這個念頭,對于她來說未必就是不愉快的事情。
阿民靠著女人家一雙手,支撐起一家的生活。這無疑也有出于“為了小廣”這樣一種至誠的愿望在內(nèi),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原因,就是在她的內(nèi)心已經(jīng)深深扎下根的遺傳的力量。阿民本是從貧瘠窮苦的山區(qū)搬到這一帶落戶的所謂“流浪者”的女兒。“你家阿民倒有和她的模樣很不相稱的氣力呀!最近我又看到她背著四大捆旱稻子走過去了!”——阿住已經(jīng)好多次聽到鄰居的老婆婆說這樣的話。
阿住為了對阿民表示感激,也在忙自己的活。領(lǐng)孫子玩,照管那頭牛,做飯,洗衣服,到鄰家去汲水等等——家里的活也不少。可是阿住照舊彎著腰,在那里高興地干活。
有一年深秋的晚上,阿民背著松葉捆,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。阿住背著廣次,正在狹窄的堂屋角落里,燒木桶里的洗澡水。
“冷吧?今天怎么回來這么晚?”
“今天比平時多干了點活。”
阿民把松葉捆扔到水槽前,連沾滿泥土的草鞋也沒脫,就走到地爐跟前。地爐里燒著一個柞樹根,正閃動著紅色的火苗。阿住想要馬上站起身來。但是由于腰上背著廣次,不抓緊木桶邊緣,就不容易站起來。
“趕緊去洗個澡吧!”
“顧不上洗澡,肚子餓呀!還是先吃點白薯吧!——有煮好的嗎,婆婆?”
阿住搖搖晃晃地走到水槽旁邊,連鍋端來煮好的白薯,放到地爐旁邊。
“早就煮好了等著你呢,涼了吧?”
兩個人把白薯穿到竹簽子上,一塊兒放到地爐上去烤。
“小廣睡得挺好吶!放到被窩里多好啊!”
“不行,今天挺冷,放下可就睡不安穩(wěn)了。”
阿民說著,大口大口地嚼著冒煙的白薯。這是只有勞動了一天的、疲勞不堪的農(nóng)民才懂得的一種吃法。將要從竹簽子上掉下的一塊白薯,被阿民一口塞到嘴里去。阿住覺得在自己的背上打著小小鼾聲的廣次沉甸甸的,同時在那里一個勁兒地烤白薯。
“像你那么干活,當(dāng)然會比別人更餓了!”
阿住不時用充滿感慨的目光盯著兒媳的臉。但是阿民什么也不說,在冒煙的柴火光亮中,貪婪地嚼著白薯。
阿民越干越不辭勞苦,不斷地?fù)?dān)起了男人的全部活計。有時候夜里還提著馬燈,順著地壟間菜。阿住對于勝過男人的兒媳,總是懷著敬意。不,與其說是敬意,還不如說是畏懼。阿民除了地里的和山上的活以外,其它的活都推給了阿住。近來甚至連她自己貼身圍的腰布也幾乎不洗了。即使是這樣,阿住從來也不訴苦,硬支撐著彎著的腰,拼命地干活。而且碰到鄰居的老婆婆,還以一副認(rèn)真的面孔夸獎兒媳:“你看,像阿民那么干,唉,俺就是什么時候死了,家里的事也用不著操心了!”
可是阿民“干活”的勁頭好像很不容易滿足。又過了一年,這次阿民提出了向河對岸的桑田發(fā)展的設(shè)想。照阿民說來,近五段步的地只能拿到十來元的地租,實在是太不合算。與其這樣,還不如把那塊地改成桑田,余暇養(yǎng)養(yǎng)蠶,只要是蠶繭的行情不落下來,一年就一定能到手一百五十元。然而阿住盡管愛錢,一想到忙上加忙,她就覺得實在受不了。特別是費工受累的養(yǎng)蠶,更是她絕對不能同意的。阿住終于帶著抱怨的語氣反對阿民了。
“這合適嗎,阿民?俺可沒有推脫的意思。雖說俺不想推脫,可是咱家沒有一個男勞力,可有個離不開人的孩子。現(xiàn)在的活就已經(jīng)累得夠戧了!你可真是想得美,養(yǎng)蠶能辦得到嗎?你哪怕替俺稍微想想看!”
阿民一聽婆婆訴苦,覺得再堅持,在情理上也太過不去。養(yǎng)蠶的念頭雖然放棄了,在栽種桑田上卻非常堅持己見。“你不用管了,桑田橫豎是我一個人干!”——阿民不服氣地看著阿住,譏諷地這么說。
從這以后,阿住又想起贅婿的事了。以前是因為擔(dān)心生活,顧慮世人說閑話,曾經(jīng)多次想招個女婿。但是這一次,是想哪怕有片刻時間能逃脫家務(wù)活的勞累而開始想招贅女婿了。正因為如此,和從前相比,這次的招婿就不知道有多么迫切了。
那恰好是橘子地里花朵盛開的時節(jié),坐在油燈跟前的阿住,透過干夜活兒戴著的大花鏡,慢慢地又談起了招婿的事。然而盤腿坐在爐旁的阿民,一邊嚼著咸豌豆,一邊說:“又是招婿,我不聽!”對婆婆連個好臉色也沒有給。
如果在以前,這么一說,阿住大體上也就算了。但是,這一次阿住硬是纏著勸說:“可是,話不能老這么說。明天是宮下安葬的日子,正好這次輪到咱們家去挖墓穴。在這種時候沒有個男勞力……”
“這有啥關(guān)系!我去挖墓穴!”
“笑話,你是個婦道人家……”
阿住本想強(qiáng)裝笑容。但是,看了阿民的臉色,她覺得貿(mào)然笑出來是太輕率了。
“婆婆,是不是你想養(yǎng)老了?”
盤腿坐著的阿民抱著膝蓋,冷冷地這么刺了一句。被突然擊中要害的阿住,不知不覺地摘下了大花鏡。而為什么要摘下來,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“啥呀?你,怎么說出了這種話!”
“你在小廣爸爸死的時候,自己說的話不會忘吧?你說如果把咱家的地分成兩份,就對不起祖先……”
“是啊!俺是這樣說過。可是,你也想想看。這不是此一時彼一時嘛,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啊……”
阿住拼命地為招進(jìn)一個男勞力而爭辯著。然而,阿住的意見連她自己聽來,也覺得站不住腳。這首先是因為她不能講出自己的真心話——也就是說,她不能道出自己是為了想過得舒服些。阿民看穿了婆婆的心思,一邊仍然嚼著咸豌豆,一邊不容情地申斥婆婆。還不只這樣,阿住過去不知道兒媳有一張?zhí)焐哪苷f會道的嘴巴,那也幫了不少忙。
“那樣對你當(dāng)然挺好呀,因為你先死啊。——可是,婆婆,你換了俺看看,總不能破罐子破摔啊!俺可不圖自己是清白啦,或者是傲氣地當(dāng)一輩子寡婦。在腰酸腿痛睡不著覺的夜里,俺也曾經(jīng)仔細(xì)想過,這么固執(zhí)己見,也是出于無可奈何。雖然說無可奈何,可是轉(zhuǎn)過念頭一想,這都是為了咱家,為了小廣,于是俺就只好咬著牙干下去了……”
阿住只是茫然望著兒媳的面孔。這時她不知不覺地弄清了一個事實。就是不管她怎么著急,直到她閉上眼睛那一天,她也不用想得到安閑。
阿住等兒媳講完話之后,重新戴上大花鏡。然后半自言自語地這樣結(jié)束了自己的談話:“可是,阿民,在世上光講大道理是行不通的,你也該仔細(xì)想想啊!俺不再說什么了!”
過了二十分鐘,不知是村里哪個年輕小伙子,用男中音唱著小調(diào),慢慢地從門前走過去了。“年輕的嫂嫂,今天來割草。草兒啊,服服帖帖,開鐮割喲!”——小調(diào)的聲音離遠(yuǎn)了后,阿住又透過老花鏡,偷偷看了一眼阿民的臉色。然而,阿民朝著油燈長長伸著兩條腿,連連打著哈欠。
“怎么樣,睡覺吧!好早點起來。”
阿民剛剛這么說完,伸手抓起一把咸豌豆,然后吃力地從爐旁站起身來……
從那以后有三四年時間,阿住默默地忍受著勞累。這好比是一匹常年勞累的馬一樣,嘗著套著軛的老馬所經(jīng)歷過的那種苦楚。阿民照樣到外邊拼命干地里的活。阿住也照樣辛勤地干著家務(wù)活。但是看不見的一根鞭子,在不斷地威逼著她。有時候因為沒有燒洗澡水,有時候因為忘記了曬稻子,有時候因為放牛,阿住經(jīng)常受到性格倔強(qiáng)的阿民的諷刺和斥責(zé)。但是,阿住從來也不還嘴,一聲不響地忍受著勞累。這首先是因為她一向就有忍從的精神,其次是因為孫子廣次比對母親更依戀奶奶。
實際上在別人眼里看來,阿住幾乎和從前一樣,沒有什么變化。如果稍有點變化的話,那只是不像從前那樣夸獎兒媳了。這樣細(xì)小的變化,并沒有特別引起別人的注意。至少是鄰居的老婆婆,還照樣說阿住是個“來世修好”的人。
盛夏的一個火熱的晌午,阿住在堆房前葡萄架的濃蔭里,和鄰居的老婆婆談閑天。四周除了牛棚里的蒼蠅嗡嗡聲外,一片寂靜。鄰居的老婆婆一邊聊天,一邊吸著短短的卷煙。這是從兒子吸完的煙頭里仔細(xì)收集起來的。
“阿民呢?哦,割干草去了嗎?年紀(jì)輕輕的,啥都肯干!”
“哪里話呀,一個女人家與其到外邊去,俺看最好還是干家里的活!”
“不呀,喜歡干地里活的人可比什么都強(qiáng)啊。俺家媳婦過門已經(jīng)七年了,別說是到地里去,就是薅草也沒干過一天呀!每天就是給孩子洗點什么啦,拆拆縫縫自己的東西啦,就這么過日子。”
“還是這樣好啊!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自己也利利落落的,現(xiàn)在時興嘛!”
“話雖這么說,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都不愿意干莊稼活吶!——喲,方才是什么聲音?”
“方才的聲音?你可真是的,那是牛放屁喲。”
“是牛放屁呀?你瞧瞧真是的。——大熱天里頂著太陽,在谷地里薅草什么的,年紀(jì)輕輕的,也夠辛苦的了!”
兩個老太婆和睦地這么閑談著。
仁太郎已經(jīng)死去八年多了,阿民用女人家一雙手支撐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同時阿民的名聲不知什么時候也傳到村子外邊去了。阿民已經(jīng)不再是起早貪黑“干活”的年輕寡婦了,更不是小伙子們的“年輕的嫂嫂”了。她卻成了媳婦的榜樣,今世節(jié)婦的模范。“你看看河對岸人家阿民!”——這樣的話和申斥一起從別人的嘴里說了出來。阿住并沒有向鄰居的老婆婆講她自己的痛苦。而且連這種想法也沒有。但是在她的內(nèi)心深處,雖然不是明確意識到,卻總有些信賴命運,她的這種信賴也終于成了泡影。現(xiàn)在除了孫子廣次以外,沒有一點指望了。阿住對已經(jīng)是十二三歲的孫子,傾注了她全部的慈愛。然而這個最后的指望,也屢次遭到挫折。
一個連續(xù)晴朗的秋日午后,懷里挾著書包的孫子廣次,急急忙忙地從學(xué)校回家了。阿住在堆房前邊正靈活地?fù)]動著菜刀,把蜂屋柿子做成柿餅。廣次的身子輕松一跳,越過一張晾曬谷子的席子,把兩腳整整齊齊地并在一起,恭恭敬敬地對奶奶行了個舉手禮,然后臉上泛著認(rèn)真的神色,沒頭沒腦地問道:
“奶奶,俺媽真的是個了不起的人嗎?”
“怎么回事?”
阿住手里拿著的菜刀停下了,眼睛緊緊地盯著孫子的面孔。
“是老師在上修身課的時候說的啊。他說,像廣次的母親那樣了不起的人,在這一帶找不出第二個來!”
“是老師說的嗎?”
“是,是老師說的。是撒謊嗎?”
阿住起初很狼狽。連學(xué)校的老師都對孫子撒這么大的謊——對阿住來說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意外的了。但是,暫短的狼狽之后,阿住突然火了,像變了一個人似地大罵阿民:“哎呀呀,撒謊啊,簡直是撒大謊!你媽那個人呀,只在外邊干活,別人就看她了不起。可是她是個心眼壞透了的人啊!你奶奶快讓她給折騰死了,她盛氣凌人……”
廣次吃驚地看著完全變了臉色的奶奶。過了一會兒,阿住又起了反作用,忽然哭了起來。
“所以啊,你奶奶是指望你才活著的呀!你可決不要忘了啊!你轉(zhuǎn)眼就到十七歲了,那時候你可馬上找個媳婦,聽見了嗎?好讓你奶奶休息休息。你媽說等征兵以后再說,這可太長啦,那怎么等得了呢!你聽見了嗎?你應(yīng)該對你奶奶盡爸爸和你兩個人的孝心呀!這樣,你奶奶也不會虧待你,奶奶什么都給你……”
“這柿子熟了也給我嗎?”
廣次貪饞地摸弄著筐子里的柿子。
“那還用說,當(dāng)然會給你啦!你年紀(jì)小,可是你啥都懂得。你可永遠(yuǎn)也不要變心啊!”
阿住哭著哭著又破涕笑了起來……
在發(fā)生這個小事件的第二天晚上,為了點小事,阿住終于和阿民發(fā)生了激烈的爭吵。這件小事,是阿住吃了阿民的白薯引起來的。然而兩個人越說越僵,阿民臉上浮著冷笑說:“你要是討厭干活,那就只好死啦!”阿住聽了馬上失去了常態(tài),像瘋了似地吼叫起來。那時廣次正枕在奶奶的膝上呼呼地睡著。阿住連孫子也不顧了,“小廣,你起來!”一邊把小廣搖晃醒來,一邊不停地罵著,“小廣,喂,你起來!小廣,喂,你起來,聽聽你媽說的什么話呀!你媽讓俺死哪!你好好聽聽!到了你媽這一輩,倒是攢了幾個錢,但是這一町三段地可都是你爺爺和奶奶開墾出來的呀!可是怎么樣呢?你媽說俺要圖享清福,就讓俺死!——告訴你阿民,俺是會死的!死沒有什么可怕的呀!不,俺可不聽你的吩咐。俺會死啊!一定會死!就是死了也纏住你!”
阿住大吵大罵,和哭起來的孫子抱在一起,而阿民照樣一下子躺在地爐旁邊,裝沒聽見。
然而阿住并沒有死。相反地在第二年立春前,自恃健壯的阿民卻得了傷寒,發(fā)病第八天就死了。當(dāng)時,在這個小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患了傷寒病。但是阿民在得病之前,為了給也是得傷寒病死掉的鐵匠辦葬禮,去干了挖墓穴的活。在葬禮那一天,鐵匠鋪里還有一個輪到要被送到隔離病院去的小徒弟。“你一定是那一天給傳染上了。”——阿住送走了醫(yī)生之后,對燒得滿面通紅的病人阿民,略微責(zé)備了一句。
阿民的葬禮那一天下著雨。但是全村的人,上至村長,全都參加了葬禮。參加葬禮的人沒有一個不惋惜早死的阿民,同時也憐憫失去了最主要勞力的廣次和阿住。特別是村代表說,郡政府原已決定近日內(nèi)對阿民的勤勞予以表彰。阿住聽了這些話,只有低下頭表示謝意。“哎,這也是命里該著呀!我們?yōu)榱吮碚冒⒚竦氖拢瑥娜ツ昃拖蚩ふ岢隽松暾垼彘L和我破費了火車錢,前后五次去找過郡長,真也是歷經(jīng)辛苦呀!可是,我們已經(jīng)斷了念頭,因此也請你死了心吧!”——為人很好的、禿頭的代表又加上了幾句詼諧的話,惹得年輕的小學(xué)教員用不愉快的眼神瞪著他。
阿民葬禮結(jié)束的那天夜里,阿住在設(shè)著佛龕的里屋一角上,和廣次睡在一張蚊帳里。如果在平時,兩個人就在黑暗沉沉里睡著了,但是,今天晚上佛龕上還點著明燈。同時舊鋪席上還飄蕩著消毒水的那種怪味。阿住可能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,翻來覆去總也睡不著。阿民的死確實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幸福。她再也用不著干活,也用不著擔(dān)心受什么斥責(zé)了。家里的儲蓄已經(jīng)有三千圓,土地有一町三段左右。從此她和孫子可以每天隨便吃大米飯了,也可以隨意買一向喜歡吃的用稻草包包著的咸鱒魚了。阿住在一生里還從來沒有這么輕松過。從來沒有這么輕松過嗎?——這使她清楚地記起了九年前的那個夜晚。那天夜里幾乎和今天夜里的輕松感覺沒有什么不同。那天是自己親骨肉的兒子結(jié)束葬禮的晚上。今天夜里呢?——今天只是剛剛結(jié)束了給自己生了一個孫子的兒媳葬禮的晚上。
阿住不由地睜開了眼睛。孫子緊挨在她的旁邊,露出一副天真的面孔,仰面朝大地睡著。阿住在端詳著這副酣睡的面孔時,漸漸地覺得她自己太悲慘了。同時也覺得和自己結(jié)了孽緣的兒子仁太郎和兒媳阿民,也都是悲慘的人。在這種感情變化中,九年間積累的憎恨和憤怒消逝了。甚至給她以慰藉的未來的幸福都消逝了。他們親屬三個人都是悲慘的人。然而,其中忍辱茍生的她自己,更是一個悲慘的人。“阿民呀,你為什么死啊?”——阿住不知不覺地對剛剛死去的人這么說著,于是淚水突然簌簌地落了下來……
阿住聽到鐘敲過四點以后,好容易才疲勞地睡著了。但是,在那個時刻,在這茅草屋頂?shù)纳峡找呀?jīng)迎來了寒冷的拂曉……
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作
呂元明 譯
經(jīng)典短篇閱讀小組
長按二維碼識別關(guān)注
9,手
手
蕭紅
在我們的同學(xué)中,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手:藍(lán)的,黑的,又好象紫的;從指甲一直變色到手腕以上。
她初來的幾天,我們叫她“怪物”。下課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著也總是繞著她。關(guān)于她的手,但也沒有一個人去問過。
教師在點名,使我們越忍越忍不住了,非笑不可了。
“李潔!”“到。”
“張楚芳!”“到。”
“徐桂真!”“到。”
迅速而有規(guī)律性的站起來一個,又坐下去一個。但每次一喊到王亞明的地方,就要費一些時間了。
“王亞明,王亞明……叫到你啦!”別的同學(xué)有時要催促她,于是她才站起來,把兩只青手垂得很直,肩頭落下去,面向著棚頂說:“到,到,到。”
不管同學(xué)們怎樣笑她,她一點也不感到慌亂,仍舊弄著椅子響,莊嚴(yán)的,似乎費掉了幾分鐘才坐下去。
有一天上英文課的時候,英文教師笑得把眼鏡脫下來在擦著眼睛:“你下次不要再答‘黑耳’了,就答‘到’吧!”
全班的同學(xué)都在笑,把地板擦得很響。
第二天的英文課,又喊到王亞明時,我們又聽到了“黑——耳——黑——耳。”
“你從前學(xué)過英文沒有?”英文教師把眼鏡移動了一下。
“不就是那英國話嗎?學(xué)是學(xué)過的,是個麻子臉先生教的……鉛筆叫‘噴絲兒’,鋼筆叫‘盆’。可是沒學(xué)過‘黑耳’。”
“here就是‘這里’的意思,你讀:here!here”喜兒,喜兒。“她又讀起”喜兒“來了。這樣的怪讀法,全課堂都笑得顫栗起來。可是王亞明,她自己卻安然地坐下去,青色的手開始翻轉(zhuǎn)著書頁。并且低聲讀了起來:”華提……賊死……阿兒……“
數(shù)學(xué)課上,她讀起算題來也和讀文章一樣:“2X+Y=……X2=……”
午餐的桌上,那青色的手已經(jīng)抓到了饅頭,她還想著“地理”課本:“墨西哥產(chǎn)白銀……云南……唔,云南的大理石。”
夜里她躲在廁所里邊讀書,天將明的時候,她就坐在樓梯口。只要有一點光亮的地方,我常遇到過她。有一天落著大雪的早晨,窗外的樹枝掛著白絨似的穗頭,在宿舍的那邊,長筒過道的盡頭,窗臺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。
“誰呢?這地方多么涼!”我的皮鞋拍打著地板,發(fā)出一種空洞洞的嗡聲,因是星期日的早晨,全個學(xué)校出現(xiàn)在特有的安寧里。一部分的同學(xué)在化著裝;一部分的同學(xué)還睡在眠床上。
還沒走到她的旁邊,我看到那攤在膝頭上的書頁被風(fēng)翻動著。
“這是誰呢?禮拜日還這樣用功!”正要喚醒她,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。
“王亞明,噯……醒醒吧……”我還沒有直接招呼過她的名字,感到生澀和直硬。
“喝喝……睡著啦!”她每逢說話總是開始鈍重的笑笑。
“華提……賊死,右……愛……”她還沒找到書上的字就讀起來。
“華提……賊死,這英國話,真難……不象咱們中國字:什么字旁,什么字頭……這個:曲里拐彎的,好象長蟲爬在腦子里,越爬越糊涂,越爬越記不住。英文先生也說不難,不難,我看你們也不難。我的腦筋笨,鄉(xiāng)下人的腦筋沒有你們那樣靈活。我的父親還不如我,他說他年青的時候,就記他這個‘王’字,記了半頓飯的工夫還沒記住。右……愛……右……阿兒……”
說完一句話,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讀起單字來。
風(fēng)車嘩啦嘩啦的響在壁上,通氣窗時時有小的雪片飛進(jìn)來,在窗臺上結(jié)著些水珠。
她的眼睛完全爬滿著紅絲條;貪婪,把持,和那青色的手一樣在爭取她那不能滿足的愿望。
在角落里,在只有一點燈光的地方我都看到過她,好象老鼠在嚙嚼什么東西似的。
她的父親第一次來看她的時候,說她胖了:“媽的,吃胖了,這里吃的比自家吃的好,是不是?好好干吧!干下三年來,不成圣人吧,也總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。”在課堂上,一個星期之內(nèi)人們都是學(xué)著王亞明的父親。第二次,她的父親又來看他,她向她父親要一雙手套。
“就把我這副給你吧!書,好好念書,要一副手套還沒有嗎?等一等,不用忙……要戴就先戴這副,開春啦!我又不常出什么門,明子,上冬咱們再買,是不是?明子!”在接見室的門口嚷嚷著,四周已經(jīng)是圍滿著同學(xué),于是他又喊著明子明子的,又說了一些事情:“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門啦,去啦兩三天啦!小肥豬每天又多加兩把豆子,胖得那樣你沒看見,耳朵都掙掙起來了,……姐姐又來家腌了兩罐子咸蔥……”
正講得他流汗的時候,女校長穿著人群站到前面去:“請到接見室里里面坐吧——”
“不用了,不用了,耽擱工夫,我也是不行的,我還就要去趕火車……
趕回去,家里一群孩子,放不下心……“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,向校長點著頭,頭上冒著氣,他就推開門出去了。好象校長把他趕走似的。可是他又轉(zhuǎn)回身來,把手套脫下來。
“爹,你戴著吧,我戴手套本來是沒用的。”
她的父親也是青色的手,比王亞明的手更大更黑。
在閱報室里,王亞明問我:“你說,是嗎?到接見室去坐下談話就要錢的嗎?”
“哪里要錢!要的什么錢!”
“你小點聲說,叫她們聽見,她們又談笑話了。”她用手掌指點著我讀著的報紙,“我父親說的,他說接見室擺著茶壺和茶碗,若進(jìn)去,怕是校役就給倒茶了,倒茶就要錢了。我說不要,他可是不信,他說連小店房進(jìn)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賞點錢,何況學(xué)堂呢?你想學(xué)堂是多么大的地方!”
校長已說過她幾次:“你的手,就洗不凈了嗎?多加點肥皂!好好洗洗,用熱水燙一燙。早操的時候,在操場上豎起來的幾百條手臂都是白的,就是你,特別呀!真特別。”女校長用她貧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觸動王亞明的青色手,看那樣子,她好象是害怕,好象微微有點抑止著呼吸,就如同讓她去接觸黑色的已經(jīng)死掉的鳥類似的。“是褪得很多了,手心可以看到皮膚了。比你來的時候強(qiáng)得多,那時候,那簡直是鐵手……你的功課趕得上了嗎?多用點功,以后,早操你就不用上,學(xué)校的墻很低,春天里散步的外國人又多,他們常常停在墻外看的。等你的手褪掉顏色再上早操吧!”校長告訴她,停止了她的早操。
“我已經(jīng)向父親要到了手套,戴起手套來不就看不見了嗎?”打開了書箱,取出她父親的手套來。
校長笑得發(fā)著咳嗽,那貧血的面孔立刻旋動著紅的顏色:“不必了!既然是不整齊,戴手套也是不整齊。”
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,校役把鈴子也打得似乎更響些,窗前的楊樹抽著芽,操場好象冒著煙似的,被太陽蒸發(fā)著。上早操的時候,那指揮官的口笛振鳴得也遠(yuǎn)了,和窗外樹叢中的人家起著回應(yīng)。
我們在跑在跳,和群鳥似的在噪雜。帶著糖質(zhì)的空氣迷漫著我們,從樹梢上面吹下來的風(fēng)混和著嫩芽的香味。被冬天枷鎖了的靈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樣舒展開來。
正當(dāng)早操剛收場的時候,忽然聽到樓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,那聲音被空氣負(fù)載著向天空響去似的:“好和暖的太陽!你們熱了吧?你們……”在抽芽的楊樹后面,那窗口站著王亞明。
等楊樹已經(jīng)長了綠葉,滿院結(jié)成了蔭影的時候,王亞明卻漸漸變成了干縮,眼睛的邊緣發(fā)著綠色,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,至于她的肩頭一點也不再顯出蠻野和強(qiáng)壯。當(dāng)她偶然出現(xiàn)在樹蔭下,那開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從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。
“我的功課,校長還說跟不上,倒也是跟不上,到年底若再跟不上,喝喝!真會留級的嗎?”她講話雖然仍和從前一樣“喝喝”的,但她的手卻開始畏縮起來,左手背在背后,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個小丘。
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她哭過,大風(fēng)在窗外倒拔著楊樹的那天,她背向著教室,也背向著我們,對著窗外的大風(fēng)哭了。那是那些參觀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,她用那已經(jīng)開始在褪著色的青手捧著眼淚。
“還哭!還哭什么?來了參觀的人,還不躲開。你自己看看,誰象你這樣特別!兩只藍(lán)手還不說,你看看,你這件上衣,快變成灰的了!別人都是藍(lán)上衣,哪有你這樣特別,太舊的衣裳顏色是不整齊的……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破壞了制服的規(guī)律性……”她一面嘴唇與嘴唇切合著,一面用她慘白的手指去撕著王亞明的領(lǐng)口:“我是叫你下樓,等參觀的走了再上來,誰叫你就站在過道呢?在過道,你想想:他們看不到你嗎?你倒戴起了這樣大的一副手套……”
說到“手套”的地方,校長的黑色漆皮鞋,那晶亮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經(jīng)落到地板上的一只:“你覺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這地方就十分好了嗎?這叫什么玩藝?”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,她看到那和馬車夫一樣肥大的手套,抑止不住的笑出聲來了。
王亞明哭了這一次,好象風(fēng)聲都停止了,她還沒有停止。
暑假以后,她又來了。夏末簡直和秋天一樣涼爽,黃昏以前的太陽染在馬路上使那些鋪路的石塊都變成了朱紅色。我們集著群在校門里的山丁樹下吃著山丁。就是這時候,王亞明坐著的馬車從“喇嘛臺”那邊嘩啦嘩啦地跑來了。只要馬車一停下,那就全然寂靜下去,她的父親搬著行李,她抱著面盆和一些零碎。走上臺階來了,我們并不立刻為她閃開,有的說著:“來啦!”
“你來啦!”有的完全向她張著嘴。
等她父親腰帶上掛著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臺階,就有人在說:“怎么!在家住了一個暑假,她的手又黑了呢?那不是和鐵一樣了嗎?”
秋季以后,宿舍搬家的那天,我才真正注意到這鐵手:我似乎已經(jīng)睡著了,但能聽到隔壁在吵叫著:“我不要她,我不和她并床……”
“我也不和她并床。”
我再細(xì)聽了一些時候,就什么也聽不清了,只聽到嗡嗡的笑聲和絞成一團(tuán)的吵嚷。夜里我偶然起來到過道去喝了一次水。長椅上睡著一個人,立刻就被我認(rèn)出來,那是王亞明。兩只黑手遮著臉孔,被子一半脫落在地板上,一半掛在她的腳上。我想她一定又是借著過道的燈光在夜里讀書,可是她的旁邊也沒有什么書本,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圍繞著她。
第二天的夜晚,校長走在王亞明的前面,一面走一面響著鼻子,她穿著床位,她用她的細(xì)手推動那一些連成排的鋪平的白床單:“這里,這里的一排七張床,只睡八個人,六張床還睡九個呢!”她翻著那被子,把它排開一點,讓王亞明把被子就夾在這地方。
王亞明的被子展開了,為著高興的緣故,她還一邊鋪著床鋪,一邊嘴里似乎打著哨子,我還從沒聽到過這個,在女學(xué)校里邊,沒有人用嘴打過哨子。
她已經(jīng)鋪好了,她坐在床上張著嘴,把下顎微微向前抬起一點,象是安然和舒暢在鎮(zhèn)壓著她似的。校長已經(jīng)下樓了,或者已經(jīng)離開了宿舍,回家去了。但,舍監(jiān)這老太太,鞋子在地板上擦擦著,頭發(fā)完全失掉了光澤,她跑來跑去:“我說,這也不行……不講衛(wèi)生,身上生著蟲類,什么人還不想躲開她呢?”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幾步,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象對著我似的:“看這被子吧!你們?nèi)バ嵋恍幔「糁哌h(yuǎn)都有氣味了……挨著她睡覺,滑稽不滑稽!誰知道……蟲類不會爬了滿身嗎?去看看,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樣子啦!”
舍監(jiān)常常講她自己的事情,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(xué)的時候,她也在日本,也算是留學(xué)。同學(xué)們問她:“學(xué)的什么呢?”
“不用專學(xué)什么!在日本說日本話,看看日本風(fēng)俗,這不也是留學(xué)嗎?”
她說話總離不了“不衛(wèi)生,滑稽不滑稽……骯臟”,她叫虱子特別要叫蟲類。
“人骯臟手也骯臟。”她的肩頭很寬,說著骯臟她把肩頭故意抬高了一下,好象寒風(fēng)忽然吹到她似的,她跑出去了。
“這樣的學(xué)生,我看校長可真是……可真是多余要……”打過熄燈鈴之后,舍監(jiān)還在過道里和別的一些同學(xué)在講說著。
第三天夜晚,王亞明又提著包袱,卷著行李,前面又是走著白臉的校長。
“我們不要,我們的人數(shù)夠啦!”
校長的指甲還沒接觸到她們的被邊時,她們就嚷了起來,并且換了一排床鋪也是嚷了起來:“我們的人數(shù)也夠啦!還多了呢!六張床,九個人,還能再加了嗎?”
“一二三四……”校長開始計算:“不夠,還可以再加一個,四張床,應(yīng)該六個人,你們只有五人……來!王亞明!”
“不,那是留給我妹妹的,她明天就來……”那個同學(xué)跑過去,把被子用手按住。
最后,校長把她帶到別的宿舍去了。
“她有虱子,我不挨著她……”
“我也不挨著她……”
“王亞明的被子沒有被里,棉花貼著身子睡,不信,校長看看!”
后來她們就開著玩笑,甚至于說出害怕王亞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。
以后,這黑手人就睡在過道的長椅上。我起得早的時候,就遇到她在卷著行李,并且提著行李下樓去。我有時也在地下儲藏室遇到她,那當(dāng)然是夜晚,所以她和我談話的時候,我都是看看墻上的影子,她搔著頭發(fā)的手,那影子印在墻上也和頭發(fā)一樣顏色。
“慣了,椅子也一樣睡,就是地板也一樣,睡覺的地方,就是睡覺,管什么好歹!念書是要緊的……我的英文,不知在考試的時候,馬先生能給我多少分?jǐn)?shù)?不夠六十分,年底要留級的嗎?”
“不要緊,一門不能夠留級。”我說。
“爹爹可是說啦!三年畢業(yè),再多半年,他也不能供給我學(xué)費……這英國話,我的舌頭可真轉(zhuǎn)不過彎來。喝喝……”
全宿舍的人都在厭煩她,雖然她是住在過道里。因為她夜里總是咳嗽著……同時在宿舍里邊她開始用顏料染著襪子和上衣。
“衣裳舊了,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樣。比方,夏季制服,染成灰色就可以當(dāng)秋季制服穿……比方,買白襪子,把它染成黑色,這都可以……”
“為什么你不買黑襪子呢?”我問她。
“黑襪子,他們是用機(jī)器染的,礬太多……不結(jié)實,一穿就破的……還是咱們自己家染的好……一雙襪子好幾毛錢……破了就破了還得了嗎?”
禮拜六的晚上,同學(xué)們用小鐵鍋煮著雞子。每個禮拜六差不多總是這樣,她們要動手燒一點東西來吃。從小鐵鍋煮好的雞子,我也看到的,是黑的,我以為那是中了毒。那端著雞子的同學(xué),幾乎把眼鏡咆哮得掉落下來:“誰干的好事!誰?這是誰?”
王亞明把面孔向著她們來到了廚房,她擁擠著別人,嘴里喝喝的:“是我,我不知道這鍋還有人用,我用它煮了兩雙襪子……喝喝……我去……”
“你去干什么?你去……”
“我去洗洗它!”
“染臭襪子的鍋還能煮雞子吃!還要它?”鐵鍋就當(dāng)著眾人在地板上光郎、光郎的跳著,人咆哮著,戴眼鏡的同學(xué)把黑色的雞子好象拋著石頭似的用力拋在地上。
人們都散開的時候,王亞明一邊拾著地板上的雞子,一邊在自己說著話:“喲!染了兩雙新襪子,鐵鍋就不要了!新襪子怎么會臭呢?”
冬天,落雪的夜里,從學(xué)校出發(fā)到宿舍去,所經(jīng)過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據(jù)了。我們向前沖著,撲著,若遇到大風(fēng),我們就風(fēng)雪中打著轉(zhuǎn),倒退著走,或者是橫著走。清早,照例又要從宿舍出發(fā),在十二月里,每個人的腳都凍木了,雖然是跑著也要凍木的。所以我們咒詛和怨恨,甚至于有的同學(xué)已經(jīng)在罵著,罵著校長是“混蛋”,不應(yīng)該把宿舍離開學(xué)校這樣遠(yuǎn),不應(yīng)該在天還不亮就讓學(xué)生們從宿舍出發(fā)。
有些天,在路上我單獨的遇到王亞明。遠(yuǎn)處的天空和遠(yuǎn)處的雪都在閃著光,月亮使得我和她踏著影子前進(jìn)。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見行人。風(fēng)吹著路旁的樹枝在發(fā)響,也時時聽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打著在呻叫。我和她談話的聲音,被零度以下的氣溫所反應(yīng)也增加了硬度。等我們的嘴唇也和我們的腿部一樣感到了不靈活,這時候,我們總是終止了談話,只聽著腳下被踏著的雪,乍乍乍的響。手在按著門鈴,腿好象就要自己脫離開,膝蓋向前時時要跪了下去似的。
我記不得哪一個早晨,腋下帶著還沒有讀過的小說,走出了宿舍,我轉(zhuǎn)過身去,把欄柵門拉緊。但心上總有些恐懼,越看遠(yuǎn)處模糊不清的房子,越聽后面在掃著的風(fēng)雪,就越害怕起來。星光是那樣微小,月亮也許落下去了,也許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。
走過一丈遠(yuǎn),又象增加了一丈似的,希望有一個過路的人出現(xiàn),但又害怕那過路人,因為在沒有月亮的夜里,只能聽到聲音而看不見人,等一看見人影那就從地面突然長了起來似的。
我踏上了學(xué)校門前的石階,心臟仍在發(fā)熱,我在按鈴的手,似乎已經(jīng)失去了力量。突然石階又有一個人走上來了:“誰?誰?”
“我!是我。”
“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嗎?”因為一路上我并沒聽到有另外的腳步聲,這使我更害怕起來。
“不,我沒走在你的后面,我來了好半天了。校役他是不給開門的,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。”
“你沒按過鈴嗎?”
“按鈴沒有用,喝喝,校役開了燈,來到門口,隔著玻璃向外看看……
可是到底他不給開。“
里邊的燈亮起來,一邊罵著似的光郎郎郎的把門給閃開了:“半夜三更叫門……該考背榜不是一樣考背榜嗎?”
“干什么?你說什么?”我這話還沒有說出來,校役就改變了態(tài)度:“蕭先生,您叫門叫了好半天了吧?”
我和王亞明一直走進(jìn)了地下室,她咳嗽著,她的臉蒼黃得幾乎是打著皺紋似的顫索了一些時候。被風(fēng)吹得而掛下來的眼淚還停留在臉上,她就打開了課本。
“校役為什么不給你開門?”我問。
“誰知道?他說來得太早,讓我回去,后來他又說校長的命令。”
“你等了多少時候了?”
“不算多大工夫,等一會,就等一會,一頓飯這個樣子。喝喝……”
她讀書的樣子完全和剛來的時候不一樣,那喉嚨漸漸窄小了似的,只是喃喃著,并且那兩邊搖動的肩頭也顯著緊縮和偏狹,背脊已經(jīng)弓了起來,胸部卻平了下去。
我讀著小說,很小的聲音讀著,怕是攪憂了她;但這是第一次,我不知道為什么這只是第一次?
她問我讀的什么小說,讀沒讀過《三國演義》?有時她也拿到手里看看書面,或是翻翻書頁。“象你們多聰明!功課連看也不看,到考試的時候也一點不怕。我就不行,也想歇一會,看看別的書……可是那就不成了……”
有一個星期日,宿舍里面空朗的,我就大聲讀著《屠場》上正是女工馬利亞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,我一面看著窗外的雪地一面讀著,覺得很感動。
王亞明站在我的背后,我一點也不知道。
“你有什么看過的書,也借給我一本,下雪天氣,實在沉悶,本地又沒有親戚,上街又沒有什么買的,又要花車錢……”
“你父親很久不來看你了嗎?”我以為她是想家了。
“哪能來!火車錢,一來回就是兩元多……再說家里也沒有人……”
我就把《屠場》放在她的手上,因為我已經(jīng)讀過了。
她笑著,“喝喝”著,她把床沿顫了兩下,她開始研究著那書的封面。
等她走出去時,我聽在過道里她也學(xué)著我把那書開頭的第一句讀得很響。
以后,我又不記得是哪一天,也許又是什么假日,總之,宿舍是空朗朗的,一直到月亮已經(jīng)照上窗子,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靜中。我聽到床頭上有沙沙的聲音,好象什么人在我的床頭摸索著,我仰過頭去,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亞明的黑手,并且把我借給她的那本書放在我的旁邊。
我問她:“看得有趣嗎?好嗎?”
起初,她并不回答我,后來她把臉孔用手掩住,她的頭發(fā)也象在抖著似的,她說:“好。”
我聽她的聲音也象在抖著,于是我坐了起來。她卻逃開了,用著那和頭發(fā)一樣顏色的手橫在臉上。
過道的長廊空朗朗的,我看著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紋。
“馬利亞,真象有這個人一樣,她倒在雪地上,我想她沒有死吧!她不會死吧……那醫(yī)生知道她是沒有錢的人,就不給她看病……喝喝!”很高的聲音她笑了,借著笑的抖動眼淚才滾落下來:“我也去請過醫(yī)生,我母親生病的時候,你看那醫(yī)生他來嗎?他先向我要馬車錢,我說錢在家里,先坐車來吧!人要不行了……你看他來嗎?他站在院心問我:”你家是干什么的?
你家開染缸房嗎?‘不知為什么,一告訴他是開’染缸房‘的,他就拉開門進(jìn)屋去了……我等他,他沒有出來,我又去敲門,他在門里面說:“不能去看這病,你回去吧!’我回來了……”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說下去,“從這時候我就照顧著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。爹爹染黑的和籃的,姐姐染紅的……姐姐定親的那年,上冬的時候,她的婆婆從鄉(xiāng)下來住在我們家里,一看到姐姐她就說:”唉呀!那殺人的手!‘從這起,爹爹就說不許某個人專染紅的;某個人專染藍(lán)的。我的手是黑的,細(xì)看才帶點紫色,那兩個妹妹也都和我一樣。“
“你的妹妹沒有讀書?”
“沒有,我將來教她們,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讀得好不好,讀不好連妹妹都對不起……染一匹布多不過三毛錢……一個月能有幾匹布來染呢?衣裳每件一毛錢,又不論大小,送來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……去掉火柴錢,去掉顏料錢……那不是嗎!我的學(xué)費……把他們在家吃咸鹽的錢都給我拿來啦……
我哪能不用心念書,我哪能?“她又去摸觸那書本。
我仍然看著地板上的花紋,我想她的眼淚比我的同情高貴得多。
還不到放寒假時,王亞明在一天的早晨,整理著手提箱和零碎,她的行李已經(jīng)束得很緊,立在墻根的地方。
并沒有人和她去告別,也沒有人和她說一聲再見。我們從宿舍出發(fā),一個一個的經(jīng)過夜里王亞明睡覺的長椅,她向我們每個人笑著,同時也好象從窗口在望著遠(yuǎn)方。我們使過道起著沉重的騷音,我們下著樓梯,經(jīng)過了院宇,在欄柵門口,王亞明也趕到了,呼喘并且張著嘴:“我的父親還沒有來,多學(xué)一點鐘是一點鐘……”她向著大家在說話一樣。
這最后的每一點鐘都使她流著汗,在英文課上她忙著用小冊子記下來黑板上所有的生字。同時讀著,同時連教師隨手寫的已經(jīng)是不必要的讀過的熟字她也記了下來,在第二點鐘地理課上她又費著力氣模仿著黑板上教師畫的地圖,她在小冊子上也畫了起來……好象所有這最末一天經(jīng)過她的思想都重要起來,都必得留下一個痕跡。
在下課的時間,我看了她的小冊子,那完全記錯了:英文字母,有的脫落一個,有的她多加上一個……她的心情已經(jīng)慌亂了。
夜里,她的父親也沒有來接她,她又在那長椅上展了被褥,只有這一次,她睡得這樣早,睡得超過平常以上的安然。頭發(fā)接近著被邊,肩頭隨著呼吸放寬了一些。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擺著書本。
早晨,太陽停在顫抖的掛著雪的樹枝上面,鳥雀剛出巢的時候,她的父親來了。停在樓梯口,他放下肩上背來的大氈靴,他用圍著脖子的白毛巾擄去胡須上的冰溜:“你落了榜嗎?你……”冰溜在樓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。
“沒有,還沒考試,校長告訴我,說我不用考啦,不能及格的……”
她的父親站在樓梯口,把臉向著墻壁,腰間掛著的白手巾動也不動。
行李拖到樓梯口了,王亞明又去提著手提箱,抱著面盆和一些零碎,她把大手套還給她的父親。
“我不要,你戴吧!”她父親的氈靴一移動就在地板上壓了幾個泥圈圈。
因為是早晨,來圍觀的同學(xué)們很少。王亞明就在輕微的笑聲里邊戴起了手套。
“穿上氈靴吧!書沒念好,別再凍掉了兩只腳。”她的父親把兩只靴子相連的皮條解開。
靴子一直掩過了她的膝蓋,她和一個趕馬車的人一樣,頭部也用白色的絨布包起。
“再來,把書回家好好讀讀再來。喝……喝。”不知道她向誰在說著。
當(dāng)她又提起了手提箱,她問她的父親:“叫來的馬車就在門外嗎?”
“馬車,什么馬車,走著上站吧……我背著行李……”
王亞明的氈靴在樓梯上撲撲地拍著。父親走在前面,變了顏色的手抓著行李的兩角。
那被朝陽拖得苗長的影子,跳動著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柵門。從窗子看去,人也好象和影子一般輕浮,只能看到他們,而聽不到關(guān)于他們的一點聲音。
出了木柵門,他們就向著遠(yuǎn)方,向著迷漫著朝陽的方向走去。
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,越遠(yuǎn)那閃光就越剛強(qiáng)。我一直看到那遠(yuǎn)處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經(jīng)典短篇閱讀小組
長按二維碼識別關(guān)注

-

-
 口蘑蟲草湯,乳腺癌病人應(yīng)該吃什么菜或者多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乳腺癌病人應(yīng)該吃什么菜或者多吃什么飲食2,口蘑和蟲草花可以一起燉豬蹄嗎3,牛肉煲蟲草花湯可以嗎4,怎么腸胃保...
口蘑蟲草湯,乳腺癌病人應(yīng)該吃什么菜或者多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乳腺癌病人應(yīng)該吃什么菜或者多吃什么飲食2,口蘑和蟲草花可以一起燉豬蹄嗎3,牛肉煲蟲草花湯可以嗎4,怎么腸胃保... -

-

-
 蟲草水丸,蟲草治支氣管哮喘如何使用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蟲草治支氣管哮喘如何使用2,魚丸能和蟲草花一起煮嗎3,慢性結(jié)腸炎中藥水丸4,蟲草丸能讓陰徑增大嗎5,蟲草鹿骨...
蟲草水丸,蟲草治支氣管哮喘如何使用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蟲草治支氣管哮喘如何使用2,魚丸能和蟲草花一起煮嗎3,慢性結(jié)腸炎中藥水丸4,蟲草丸能讓陰徑增大嗎5,蟲草鹿骨... -
 蟲草漲奶,我補(bǔ)乳期因為奶水不好問一下各位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我補(bǔ)乳期因為奶水不好問一下各位寶媽們冬蟲草泡水可以吃嗎2,油炸魚肚的做法油炸過的魚肚怎么做才好吃3,蟲草花是...
蟲草漲奶,我補(bǔ)乳期因為奶水不好問一下各位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我補(bǔ)乳期因為奶水不好問一下各位寶媽們冬蟲草泡水可以吃嗎2,油炸魚肚的做法油炸過的魚肚怎么做才好吃3,蟲草花是... -
 蟲草雙笙九,雙笙的微博叫什么名字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雙笙的微博叫什么名字2,雙笙有一首歌歌詞是什么什么環(huán)游知否知否3,蟲草雙參酒為什么賣那么貴4,寒衫浮夢雙笙新...
蟲草雙笙九,雙笙的微博叫什么名字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雙笙的微博叫什么名字2,雙笙有一首歌歌詞是什么什么環(huán)游知否知否3,蟲草雙參酒為什么賣那么貴4,寒衫浮夢雙笙新... -
 北蟲草學(xué)名,北蟲草是什么東西是否可種植可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北蟲草是什么東西是否可種植可否種植賺錢2,蟲草花本名為蛹蟲草又被稱為北蟲草蟲草花的功效是什么呢3,南蟲草花與...
北蟲草學(xué)名,北蟲草是什么東西是否可種植可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北蟲草是什么東西是否可種植可否種植賺錢2,蟲草花本名為蛹蟲草又被稱為北蟲草蟲草花的功效是什么呢3,南蟲草花與... -
 北蟲草中毒,直接食用冬蟲夏草真的會中毒嗎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直接食用冬蟲夏草真的會中毒嗎2,種植北蟲草大棚內(nèi)有有毒氣體嗎我在北蟲草大棚內(nèi)干活感覺壓氣氣短3,種植北蟲草大...
北蟲草中毒,直接食用冬蟲夏草真的會中毒嗎...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直接食用冬蟲夏草真的會中毒嗎2,種植北蟲草大棚內(nèi)有有毒氣體嗎我在北蟲草大棚內(nèi)干活感覺壓氣氣短3,種植北蟲草大... -
 納米蟲草膠囊,蟲草膠囊功效一樣么哪種最好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蟲草膠囊功效一樣么哪種最好2,蟲草膠囊的功效與作用及食用方法3,金蟲草雙參膠囊的藥理作用4,蟲草膠囊對氣管炎...
納米蟲草膠囊,蟲草膠囊功效一樣么哪種最好2022-10-17 09:01本文目錄一覽蟲草膠囊功效一樣么哪種最好2,蟲草膠囊的功效與作用及食用方法3,金蟲草雙參膠囊的藥理作用4,蟲草膠囊對氣管炎...